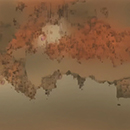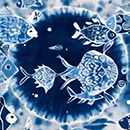“数字中国”生成式AI艺术
文/于幸泽
在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下,同济大学主办的2024年“数字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人才培训项目圆满结束,此次展览汇聚了40位学员的13组“数智艺心”之作,这些作品不仅是艺术与技术交融的结晶,更是对未来艺术探索的一次勇敢尝试。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批在人工智能与艺术领域具有深厚造诣的导师。他们不仅为学员们传授了前沿的知识与技能,更以自身的理论研究和艺术实践为学员们树立了榜样。在此,我们特别感谢以下导师的辛勤付出与无私奉献(排名按讲课先后顺序):运迪、于幸泽、袁烽、李磊、罗霄、解学芳、刘旭光、孙澄宇、蒋飞、范凌、张周捷、林俊廷、周洪涛、齐鹏、胡炜、戴开宇、王祥等。还要感谢在培训期间来自科技企业和数字艺术设计产业专家们的精彩分享。
学员们的作品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展现了人工智能艺术的无限魅力,更体现了他们对“数字中国”主题的深刻理解和创新表达。通过此次展览,希望能够激发更多人对人工智能艺术的关注与热爱,共同推动这一新兴艺术领域的繁荣发展。这种由蓝变白的过程似乎象征着穿着它们的工人生活进 步的梦想。该装置作品的标题也用社会学中熟悉的术语来指代了这一点。这种进步 带来了更大的社会义务和责任,但也带来了更大的个体自由。另一方面,即使蓝色 工服承诺务工者被一个工作集体所接纳,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德国欧宝 美术馆的策展人将刘广云的《被褪色的工服》与约瑟夫·博伊斯的《奥威尔的腿 ——21世纪的裤子》放在同一个展厅展出,体现了策展的技巧和敏锐。在乔治·奥 威尔的小说《 1984》出版35年后的1984年一月份约瑟夫·博伊斯在“早安,奥威尔 先生”表演期间,他穿的就是“奥威尔裤子”。这一动作是媒体艺术家白南准Nam June Paik的电视实验,由巴黎蓬皮杜中心在全球范围内播出。 Beuys和其他参与 者穿着牛仔裤,有两个圆孔——一个在右膝,一个在膝盖后部,博伊斯说: “世界 上每个人都应该做这样的裤子来反思全球的物质主义。
肖像 刘广云之前的作品本质上是关于人的自主性,而《肖像》(2019)的主题则 体现了当代艺术家本人在作品创作中的自主性。这往往是由传统的力量而引申出来 的,刘广云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经历过这一点。在中国,艺术家的训练仍然由传统 为基础的,艺术史的例子以及对某些技巧的掌握决定了学院的美学标准。古代、文 艺复兴和古典主义的正式规训体系实际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刘广云对这一时期 的作品进行批判性修改时,这无异于是一种反叛。
刘广云在《肖像》中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处理作为教学练习的古代著名雕塑的石膏模 型,这些雕像展示了维纳斯和阿波罗或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他用锯 子将作品切成均匀的薄片,以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度拆解了这些雕像。然后,他将雕 像打散的各个部分用钩子连接起来并挂在墙上,以此方式消解了雕像的神圣性并进 一步强化了这种舶来品的商品特征。
切片 这种行为所表达出的对古典形式理想的反叛在西方现代性中具有传统。它经 常发生在对丑陋、奇异和怪诞的崇拜中,这种崇拜往往趋于无形。刘广云的作品却 并非如此。因为他用一种形式代替了另一种形式,他在粗暴地解构传统审美的同时 衍生出来另一种美学。作品的常规切割展现了雕塑经过加工的光滑外观和未经加工 的粗糙内部。美的概念,其标志就是碎片。T.S.艾略特在他的史诗《荒原》中也讲 述了这一点。它说我们今天手里的东西“只是一堆破碎的图像”。将它们组合成一个 整体是观众的工作。这给我们带来了切片的另一个功能,它补充了艺术家的作品(生 产美学)和观众的参与(接受美学)。今天,由艺术家通过他的作品向我们提出问 题: “我们必须自己寻找答案”,1921年,贝尔托·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在剧 院的墙壁上写下了这句话,欢迎前来观看他的首部戏剧演出的游客。这不是为了娱 乐,而是为了让观众一起思考。那些在那里并留下来的人经历了史诗戏剧的诞生。
滲泡 刘广云为他的社交软件上的朋友圈建造的另一个装置纪念碑《滲泡》(2024)。这件装置作品由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朋友和熟人的头像照片组成,有些 是黑白的,有些是彩色的。杯子也是统一格式,一半盛茶,一半盛酒。茶和酒的选 择最具象征意义。尽管我们全球的消费习惯变得越来越相似,但茶仍然是中国人的 最日常饮品,而葡萄酒则也是欧洲人的最佳选择。这微妙地表明,艺术家在选择朋 友和熟人时没有任何民族主义区分。并通过他的艺术作品重新识别他们,他遵循一 种与网络安全截然相反的开放和自由,他在公开与私密中建立了一种熟悉与陌生的 关系,与此同时,刘广云作品中出现的网友头像也通过形象的反相处理和水的折射 发生形状变异预示了某种识别上的差距。当艺术家让他的社交圈朋友和熟人组成500个玻璃杯以装置的形式展示时,这种印象更加强烈。同时,这也是一种特别的 审美体验,其对称性、比例和色彩都让人想起极简主义艺术作品。茶和酒的排列方 式使观者的目光或由浅入深,由深至浅,渐变而细致的色调过渡。同时,参观装置 也是一次联觉体验,空气中可能还弥漫着茶和酒的香气。
电热被 这个装置作品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台词。我们看到的是白色棉被和金色 被罩。被面上散布着电缆和电线,其中一些暴露在外,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被面 上的灯泡是互动,一旦观众靠近装置,传感器就会向灯发送信号,灯就会亮起来。 乍一看,整个布置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带有电线的棉被,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呢? 就像人们理解超现实作品或梦境一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在分析时, 梦会遵循它们自己非常精确的语言。因此,超现实主义者宣称精神分析学家是他们 自己的一员。棉被是人们最私密、最贴身的物品之一,它还具有温暖和保护的含义。 显然与该装置中的危险相关的电线系统是完全相悖的,或许艺术家想告诉我们离我 们最近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最安全的。
刘广云三十年来游走于中国和德国之间,他是一个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旅行者。 尽管他在很多作品中显示了这种生活认知上的丰富性,但他却无法在这种中间状态 中安定下来,这也让他回答自我存在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它像一个通奏的低音一 样始终贯穿在艺术家的作品里。不言而喻,这并不只是刘广云的个人状态,当我们 说“我”时,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提出并强调了自我存在的处境也从艺术家那里一直 延展到我们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