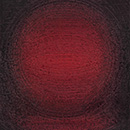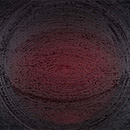开放中广延:杨黎明的频率变动
文/杜曦云
“书,心画也。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西汉·扬雄)中国的书法和人的心灵状态紧密相连,书写的过程其实是陶冶心灵的过程。于是,书写同时成就了人的心灵状态和书法的视觉效果。从中国传统书法中脱胎而出,杨黎明用毛笔饱蘸着稀薄的油彩,画出无数根震动的线条。这些线条在艺术家下意识的挥洒中,遵循着特定的秩序游弋,显现为明确的画面结构。
依靠难以言说的本能,杨黎明很早就遵循心灵感应来作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内心有一个声音、内在有一个能量在引导、牵引着我。于是,绘画的过程就是他倾听这超验的声音,顺应这无形的能量,向着茫茫未知一路前行。前行中并没有预先的规划,等到暂歇时回望,才看到了已经蹚出的清晰路径。
起初,热血激情驱动的蓝色曲线剧烈震颤,混杂无所顾忌的各种实验,尽情尽性地抛掷到二维平面上,汇聚成蓝色的海洋。起伏浮沉的蓝海开放地容纳他的激越和试错,鲜活起来,平静下去……
随着经历和认知的累积,他的绘画越来越沉郁凝滞,画面也由幽蓝转为黝黑。敏感于个人处境,广延到家国情怀乃至冥冥中的宿命意识,他环顾当下并回溯着历史,在仰观俯察中心有戚戚,悲天悯人之情绵延不绝。
在专注于黑色的那些岁月中,他沉潜到心灵深处,廓清自身的文化基因,激活本土的历史记忆,从当下的生存感受出发,把各种复杂的因素统统融汇到无法化解的浓稠黑色中,以致画面混沌渺茫、无言以对。
生命中的契机出乎意料,但又不期而至。持续多年的黑色画面里,忽然出现了一缕光亮,杨黎明紧追不舍,在一笔笔、一幅幅中确认和扩展着光亮,色彩也由黝黑渐变为暗红乃至殷红。红色依然是心思意念的复杂结晶,具体而微的笔触和汇集而成的结构中,有剧痛、狂怒、大悲、绝望,但也有酣畅、狂喜、挚爱、销魂,以及宁静和盼望。很难条分缕析艺术家的情绪和思路,它们在书写的过程中随机释放出来,艺术家自身可能都是不由自主的。人希望有“自知之明”,但往往是在面对未知甚至涉险时的本能行为,才闪现出了人的真相。杨黎明的红色系列绘画,是纵情,是自律,是冒险,是谨守,是沉溺,是超越,是缠斗,是解脱……绘画时的纵横捭阖,和生活中的起伏辗转相互影响,积淀到他流转不息的内心世界中。
心灵的走向和需求,是奇妙流变的。近期,杨黎明决然走出了红色,进入无垠的白色世界中,这是他继续聆听内心声音的后果。独自摸索的他,依然难以辨析自己为何要如此,但身心本能地有舒适自得感。他在不断确认这种感觉的过程中,寻找和靠近最佳状态。他感应着意识的流转,尽量保持“气沉丹田”,以求心胸空灵、脑海轻盈。这种身心状态转化为画面的构图,穹顶般的长弧线厚实地支撑着画面下部,画面上部越来越单纯光洁……
听凭内心声音的指引,杨黎明的画面转化着他的心灵形态和波动频率,成为描摹心灵的“写实绘画”。从蓝色开始,经历黑色和红色,当下的他正在白色系列中向无限的光洁开放。杨黎明如此自述:“未来,我不知道这团白光会带我走向何方,但我只知道我将继续在这个领域内、在这个状态中,尽可能走得更远。”这是自身本能的驱使,还是冥冥中天意的指引?他将走向何方?面对万古长空和莫测命运时,每个人各有反应,关联到各自心底的终极信靠。